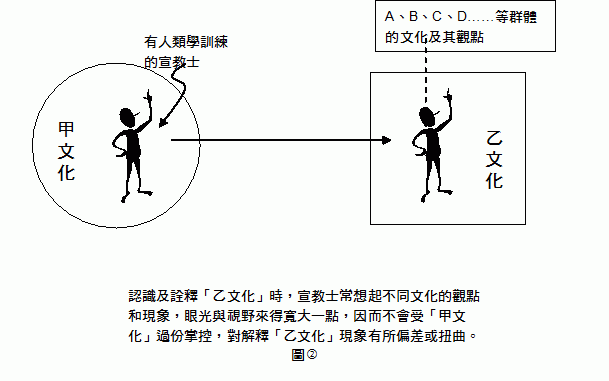|
主題文章 01 人類學與宣教 連達傑牧師 ─香港浸信會聯會差傳中心主任 |
|
引言 2003年九月,筆者排除萬難,在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以兼讀方式修讀了一個有關「人類學」的碩士課程(M.A. in Anthropology)。每當有牧者同工或肢體知道後,他們都顯得有點錯愕,不曉得如何去理解這事。對筆者來說,這確是一條嶄新的道路,它帶來了不少的衝擊和挑戰。然則,人類學與筆者原有的宣教訓練背景真是毫無關係的嗎?那又不然!其實彼此是息息相關的。本文就嘗試去解答這個問題。
從兩個例證說起 首先,讓我們看看一份知名的福音派宣教期刊《宣教學:國際評論》(Missiology : An International Review)。它的創辦年是1973年,它是「平地一聲雷」而創立的嗎?不是的;因它其實是沿自另一份期刊《實踐人類學》(Practical Anthropology)而來的。有十九年之久(1953 – 1972),一些聖經翻譯學者如:E.A. Nida, W.A. Smalley, J.A. Loewen及W.D. Reyburn等人,紛紛透過《實踐人類學》這份刊物,鼓勵教會去認識到,人類學研究所帶來的亮光,確是對基督教宣教有所幫助的。事實上,他們也具體地分享了人類學這學科中的語言研究,可怎樣去幫助聖經的翻譯工作。[1]對他們來說,《宣教學:國際評論》是承繼《實踐人類學》而再上路的。
其次,讓我們看看影響普世教會深遠的美國福樂神學院「世界宣教學院」(School of World Mission)。打從1965年創立以來,在教務人員名單上,就曾有很多位教授都是人類學出身,或是對人類學有深入研究的。例如:Alan Tippetts, Charles Kraft, Paul Hiebert, Sherwood Lingenfelter及Dan Shaw等學者就是了。這樣看來,強於宣教訓練與強於人類學裝備並非毫無關係吧!
筆者述說以上這兩個例證,不外想指出一個要點:人類學與基督教宣教學確是緊扣在一起的;人類學對宣教學、宣教事工、宣教工場及宣教士本人等,都會帶來相當大的貢獻和幫助!
人類學是什麼 既說人類學是那麼重要,那究竟它是怎麼樣的一門學問呢?要了解其意涵,可先從英文名稱 “Anthropology”入手。它本由兩個希臘文字組成,其一是 “anthropos”(意思是「人」或「人類」),其二則是“logos”(意思是「研究」)。推而論之,「人類學」原來的意思就是研究人的一門學問。然則,其他有些學科不也是研究人的麼?例如:社會學、生物學、心理學、哲學或歷史學等。人類學與它們的分別何在呢?要明白彼此間的分別,可從以下人類學的三大特色來觀察之:[2]
其一,人類學是從一個「整全的角度」(holistic view)去認識人;它並不像其他學科僅從某個觀點去掌握人的本質。人類學是整全地透過不同角度去看人類群體的文化生活狀況。隨手檢起一本關於「文化人類學」的導論書,就會發現它總是從政治、社會、民族、宗教、經濟及家庭等角度去詮釋人的種種行為,並其背後的思想、信念和系統。還有,對於「人」的意涵,人類學的觀點可以並非專指某個民族群體,而是泛指古往今來(時間上)及普天之下(空間上)的「人類」;它要尋找人的共同點,「整全性」的意義也在此顯明了。
其二,因著以上的理解,人類學的進路也必然是「比較性」的(comparative approach)。它先去面對全球群體的不同文化,經過觀察、比較、比對後,然後才引伸出一些判語、準則和觀點。換言之,其論點是採用「跨文化的角度」(cross-cultural perspective)。因此,真正認識人類學的人,其「文化觀」是較寬大和多角度的;雖常有機會發現別的文化與自己所屬的有所差異,卻仍努力持守「尊重別民族文化」的態度;這也就是一種「文化相對主義」(cultural relativism)的取向了。
其三,人類學者十分重視實地考察的工作,他們不會滿意自己只局限在實驗室或圖書館去研究人的文化及經驗。一般來說,他們可以花上幾個月、一年半載,甚或更長的時間生活在某些群體中,為的是去尋找第一手的經驗與體會,好正確地掌握別個民族的文化內涵和意義。簡言之,「田野研究」(fieldwork)是人類學知識發展的重要基礎。
至於作為一門正式學問,從歷史的角度看,人類學大概源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並二十世紀初期,一些英美學者如:Edward Tyler(1832–1917),Lewis Henry Morgan(1818–81),Bronislaw Malinowski(1884–1942),A.R. Radcliffe-Brown(1881–1955)及Franz Boas(1858–1942)等人,他們對非西方社會、沒有文字及科技上不大發達的民族群體進行研究—或是重視其整全的文化層面,或是專注其社會結構方面;或是以單一群體作為研究對象,或是以多群體比較方式去進行等。他們累積下來的觀點、方法、經驗與知識,就逐漸奠定了現代人類學發展的基礎。其後,隨著二十世紀的演進,加上以下這些大師的創新和整合,如:Alfred Kroeber(1876 – 1960),Ruth Benedict(1887–1948) ,Edward Sapir(1884–1939) ,Margaret Mead(1901–78) ,Raymond Firth(1901–2002) ,Edward Evans-Pritchard(1902–73) ,Leslie White(1900–75) ,Marvin Harris(1927–2001) ,Claude Levi-Strauss(1908– ) ,Mary Douglas(1921–2007)及Clifford Geertz(1926–2006)等人,這門學問也不斷的深化和開拓。大體而言,人類學研究可包括以下四大範疇: 1. 體質人類學(Physical Anthropology) 從生物有機體的角度來研究人類,透過出土的化石遺跡,研究人類的起源及其演化至今的過程,並探討人的「體質特徵」究竟是如何形成及為何會如此。體質人類學者有別於比較生物學者,主要在於前者是較多注意文化及環境方面對人所產生的影響。 2. 文化人類學(Cultural Anthropology)[3] 研究當代某些群體的文化、思想、行為,並整理成一個完整的報告稱作「民族誌」(ethnography);或廣泛地透過比較方式,研究一般人類社會文化方面的概況、特色及模式等,可稱作「民族學」(ethnology)。 3. 語言人類學(Linguistic Anthropology) 探討人類過去及現在的說話及語言系統。它分別從「歷史角度」研究語言的起源,從「結構角度」看發音、文法及語意等,及從「社會處境角度」認識語言與社會文化的關係。 4. 考古學(Archaeology) 基於出土的古蹟文物及人工製品,研究沒有文字記載時代的「物質文化」,從而推論、甚至重組史前人類社會的文化形態及生活習慣。
以上劃分的四大範疇、四大分支(subfields),可算是一個傳統的共識,但當今這門學問還逐漸孕育出一個新的方向,衍生著一個新的研究範疇,就是「應用人類學」(Applied Anthropology)——把人類學所得的亮光與知識,應用在全球各地不同的文化或次文化群體中,加以研究,以求解決當代一些社會及文化的問題。舉例說,研究芝加哥城市中的「街頭幫派」(street gangs),探討洛杉磯多元民族的學校教育系統,或「麥當奴快餐文化」在世界不同城市中的彰顯形態等就屬這一類了。
我們必須留意的,上述各大範疇相互間仍有緊密的結連,並非界線分明,毫無關係。還有,無論劃分為四大範疇或五大範疇,我們都可注意到,人類學這門學科,其實是希望從「生物角度」(biological perspective,如體質人類學)及「文化角度」(cultural perspective,如文化人類學、語言人類學、考古學及應用人類學)這兩大層面去理解人類的起源、本質、演化及其過去的和當今的社會文化形態等等。並且,不論古今、何種形式及那個地域,大凡在地球上曾出現過的人群,都可成為人類學者研究的對象。由此可見,人類學研究所涉及的範圍是最廣闊的,也是最跨越時空的!
人類學對宣教的貢獻 過去,人類學者像基督教宣教士一樣,往普天下去,進入不同的文化群體中。所不同者,乃是他/她要作文化研究,而不是去傳揚基督的信仰。然而,他們的研究結果實對基督教宣教大有幫助。先前我們簡略解說「何謂人類學」時,相信大家已稍為感受到它的好處。現在我們嘗試對這方面作進一步的分析。
我們可以說,「人類學」是十分有用的「觀念工具」(conceptual tools),它幫助從事宣教的人得以認識其他群體的文化。宣教士離鄉別井,進入全球各地不同的民族中,他們首先發現的,除了是自己在地域上身處異鄉外,更重要的,是他們在新處境中要與差異甚大的文化相遇。怎樣去瞭解這個民族群體及其文化,以便去服事他們並分享基督的愛,就成了一個逼切的課題。由於人類學的研究焦點本來就是「人的文化」,它就正好提供了適切的內容與方法,幫助宣教士展開這個認識別文化的歷程。
如眾周知,每一個民族文化自有其世界觀、價值觀、生活方式及行為準則等,生活在其中的人,自幼便在成長的過程中透過學習而曉得。惟作為成人的宣教士並非以這種「從小就接受薰陶」的方式去認識及吸收該文化。尤有甚者,叫問題更趨於複雜的,就是他/她本身還帶有另一套的文化去進入別的文化中。這樣,他/她該怎樣才可以有效地、成功地和客觀地認識並欣賞別的文化呢?(見圖) 人類學在這裡就發揮了它的作用!
由於人類學的學問內容是建基於對眾多民族、文化所得資料進行研究而產生的,並透過深入探索及比較異同等途徑,才引伸出(to generalize)其理論和觀點。可見,人類學本身一開始就採用「跨文化的進路」(cross-cultural approach),其視野則是「跨文化處境」(cross-cultural settings)。因此,宣教士若有了人類學的訓練,一方面可以有一套適切的觀念、工具和方法,幫助自己更有效地掌握及明白身處的新文化的內涵,另方面他/她則學懂了帶著「跨文化觀點」(cross-cultural perspective)去看工場上的種種問題,不會局限於自己原有的文化觀點(mono-cultural perspective)。這樣,宣教士就可避免因有太強的「文化排他性」(即所謂「我族中心主義」[ethnocentrism])而損害了自己與當地人的關係和福音工作的建立。(見圖)
以上所說的都是從大處著眼,叫我們認識人類學在基督教宣教上的價值和益處。具體來說,我們看見它可以:幫助聖經的翻譯事工;啟發聖經學者對聖經的文化處境有新的認識;[4]提供「世界觀」(worldview)及「形式與意義」(form and meaning)的概念,使宣教士傳遞真理話語時更能適切當地的民情和需要;協助宣教士運用「參與觀察法」(participant observation)及「局內與局外人觀點法」(emic and etic approach)來深入瞭解一個群體的生活與行為等等……[5]
結語 我們都曉得,按著聖經一貫的主題,神要差遣祂的子民(教會)由近而遠(徒一:8)「往普天下去」(可十六:15)傳揚救恩的信息,這是從地理地域的角度而說的。但若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去看,其實我們要做的,是要在世界中向「萬民」述說引領人作基督門徒的福音(太廿八:19);所蘊含的意思,就是我們需要按著不同文化處境實況去向不同的群體作見證,不要在內容形式上千篇一律,或是強把自己慣常的一套加諸別人。保羅正是這方面的典範,向甚麼樣的人,他就作甚麼樣的人,為的是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(參見林前九:19-23)。看來,作為傳播基督信仰的宣教士必須留意這一點!
人類學這學科,是一門關心人類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學科。它雖然不是一服「萬靈丹」,叫我們可解決一切宣教工場上所遇見的文化困難和問題,但它確是十分有用的工具,幫助教會成功地在不同文化群體中推進福音的工作。人類學對世界上「萬民萬族」所作的研究,並其所提供的資料和亮光,都可大大提升教會宣教的能力及加強教會對世界的認識。而當教會不斷的吸收人類學的資源,加上結合真理知識,並神學及經驗上的反省,就可發展為「應用人類學」的其中一支派,可稱為「宣教人類學」(Missiological Anthropology)。[6]教會有了這樣美好的「屬靈武器」,能夠「知己知彼」,相信就易於「百戰百勝」了!(見圖)
筆者深深的相信,華人教會若想在廿一世紀接觸更多民族群體,大力發展宣教事工,並且帶來果效,她不能迴避普世各地不同群體的文化問題和對應之道。人類學似乎提供了一條「通道」,凡關心宣教者看來必須倍加注意!
[1] Norman E. Allison, “The Contribu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o Missiology”, in Edward Rommen and Gary Corwin eds., Missi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(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Series Number 4), Pasadena, CA : William Carey Library, 1996, P.31. [2] 參考Robert H. Lavenda and Emily A. Schultz, Core Concept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(Second Edition), Boston : McGraw-Hill Companies, Inc. 2003, pp.2-3. [3] 美國的學問傳統多使用「文化人類學」這名稱,但英法的學問傳統則多稱作「社會人類學」(social anthropology)或「「社會文化人類學」(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)。兩大傳統的研究重點雖各有不同,但整體上仍屬同一範疇(參閱王銘銘,《人類學是什麼》,台北:揚智文化,2003,頁13-14, 20-21)。另外,由於「文化人類學」的研究焦點在於文化,而「人類學」整體上最大的貢獻也在於文化層面,所以,作為分支之一的「文化人類學」,很多時候也普遍被稱為「人類學」(見Norman E. Allison, “The Contribu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o Missiology”, P.31)。 [4] 關於聖經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,以下三本書籍可作參考:Jacob A. Loewen, The Bible in Cross-Cultural Perspective, Pasadena, CA : William Carey Library, 2000; Thomas W. Overholt,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the Old Testament, Minneapolis, MN : Fortress Press, 1996; Bruce J. Malina, The New Testament World : Insights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(Third Edition, Revised and Expanded), Louisville, Kentucky :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, 2001. [5] 若想深入了解文化人類學對宣教的貢獻,除了上述注1提及Norman E. Allison之文章外,另可參考Charles H. Kraft, Anthropology for Christian Witness, Maryknoll, New York : Orbis Books, 1996, Chapter 1 “Why Anthropology for Cross-Cultural Witnesses?”, Stephen A. Grunlan and Marvin K. Mayers, Cultural Anthropology –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(Second Edition), Grand Rapids, Michigan :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, 1988, Chapter 1 “Anthropology and Missions”. [6] Louis J. Luzbetak, The Church and Cultures : New Perspectives in Missioological Anthropology, Maryknoll, New York : Orbis Books, 1988, pp.12-63.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十二期,2008年四月。 |